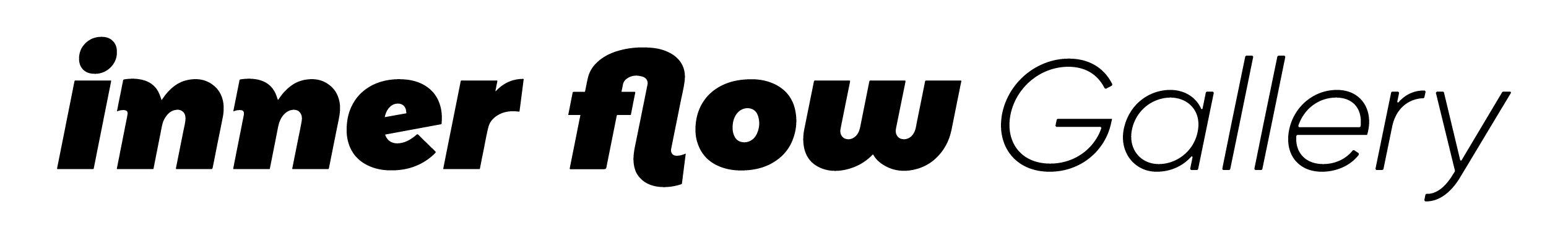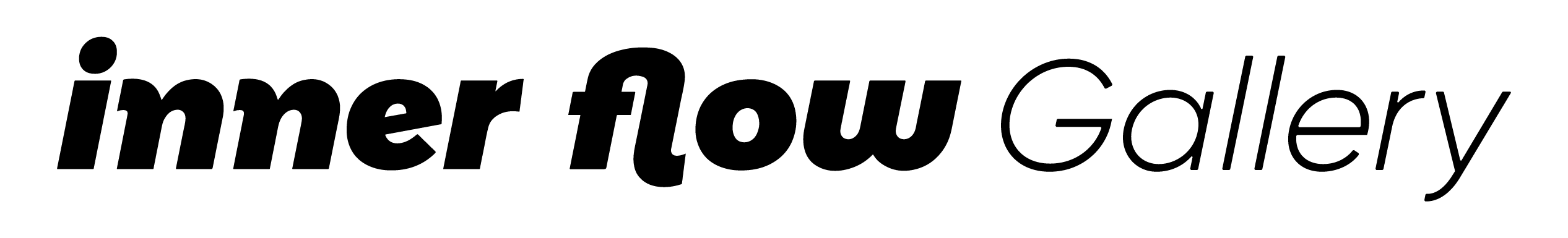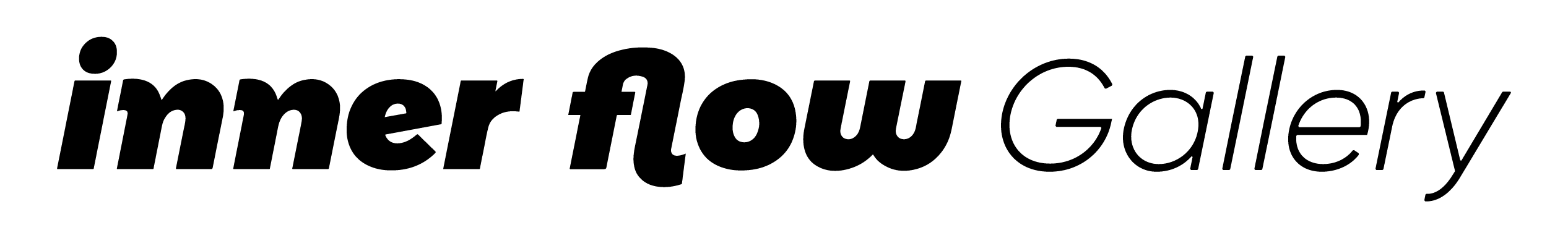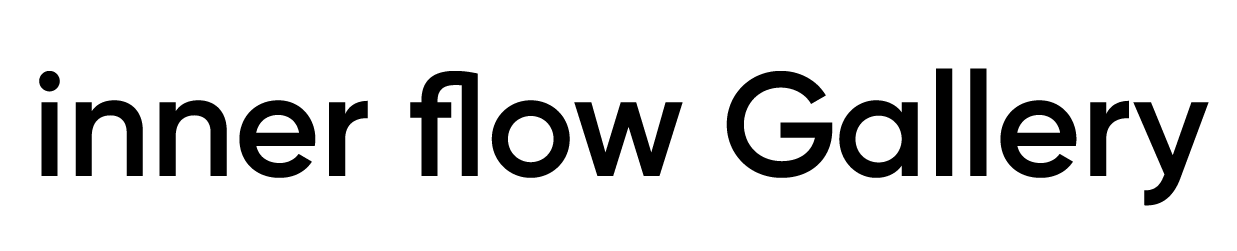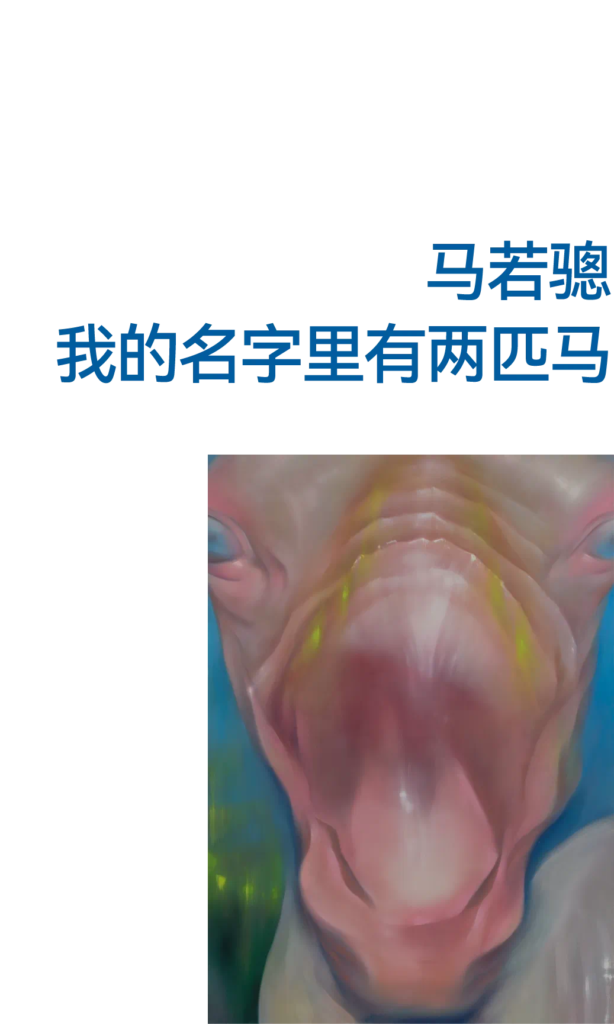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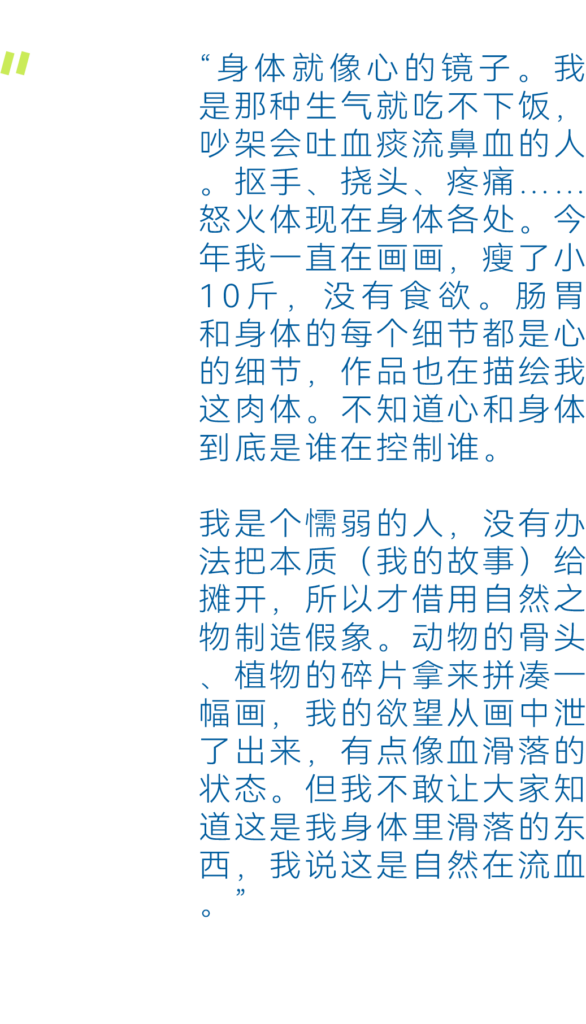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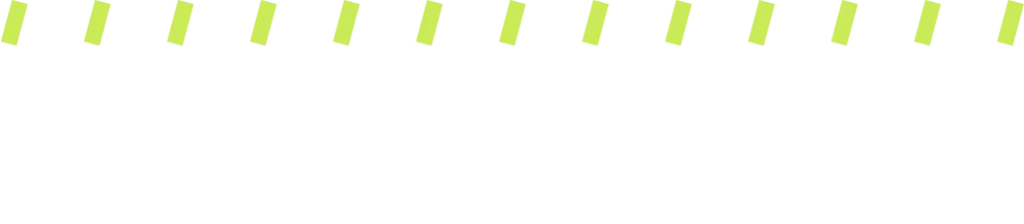


十多度的北京虽然阳光明媚,风却已转凉,怕冷的人穿上了厚外套,为了维持一如既往的温暖。一袭深黑色长裙,让马若骢在空旷的工作室里显得格外单薄。她就住在这里,一天画十个小时,生活和工作很难分开。
采访全程,我的注意力很少脱离沙发对面的马若骢,她犀利、果断,清醒地袒露自己和画的遭遇。顿挫的观点如庖丁解牛,一刀一刀拥抱具体的痛苦。
一切轻描淡写的疼痛都值得我们反思。马若骢说自己是一个懦弱的人,在我看来她的懦弱是一股劲儿。骨子里的反叛与野心,化为尖锐的颜料,在光滑的肌肤上堆出“火焰峰”,割开人性的残酷真相。
艺术家谈起极度敏感的身体和情绪,让我想到作家韩江——看一部关于奥斯维辛的电影时会恶心呕吐,接连难受好几天;写一本以苦难为背景的小说,每天走在路上都会哭。同为女性,她们正在用“流血的眼睛”直面暴力。



“马若骢:丰溢之血”
inner flow Gallery展览现场
生活没有变化,画风却变了。本科时期,马若骢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学习插画。那时的她大胆、直接,女性的裸体在她笔下从来不是一种禁忌。研究生时去往英国,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钻研雕塑。环境对审美的影响将她继续往前推,“我认可了新的画法(英式笔触),追求更表现、抽象,更松散、诙谐、黑色幽默”,转而用流淌的油画质感塑造细腻、忧郁和更有冲击力的画面。
“从具象往表现转型的过程中,有很多废掉的作品,没有在公共场合展示过,后来就回国了。起初去了上海,那个时期(疫情前后)诞生了我目前创作的雏形。”这中间并没有关键的转变因素,只是“积累几年后也该画出个结果了”。
马若骢毫不掩饰地说:“我画的从来都是自画像,是我的欲望。这些东西在画布上的表达是一种‘泄掉’的感觉。”回国后的创作,那些对女人体的变形和夸张化的二次处理,开始接近她所预谋的“假象”。

《骄傲的春血 Proud Spring Blood》
140×100cm 布面丙烯、油画 2024

本科求学期间,SVA大一Painting教授Nancy Chunn说过一句话:“艺术家永远不要爱上自己的作品。”这句话本来平平无奇,只是老师上课随口聊天说的,却随着时间推移莫名地刻在马若骢的心底。
每画一幅新画,就会无法再爱上旧画。她永远对现在进行时的事物有着“发烧般的迷恋”。当一幅画完成的瞬间,迷恋会消失。“喜新厌旧是我控制不了的事,它是一种推着我走的力量。”
“我一般会同时启动5幅画,就能知道哪些画是我爱的,哪些是不那么爱的。5幅里面大概率会有3幅被盖掉。”艺术家将画视为爱人,但这些画也在彼此竞争,留下来的才会得到更多的爱。

《上弦月 First Quarter Moon》
140×100cm 布面丙烯、油画 2024
爱欲和怒火,填满了身体。正如展览的标题“丰溢之血”,是马若骢继“肉身”和“对视”系列后,延伸出的基于私人经验“爱时经血更浓郁”的新隐喻。
血液在供给生命动力的同时,充斥疾病、不洁、赎罪、诞生等意味。神圣的血红色引向一条禁忌之路,沿途的祭台把生死、暴力、诱惑、幻想依次排开,完成一场献祭仪式。
“我是一个载体,我认识的人、我对身边人说的话,朋友、恋人、陌生人……所有事物都将从我的身体里流过,流出来的就是我的画。”

《日日是好日 Everyday is good day》
140×100cm 布面丙烯、油画 2024

《爱欲丰盈 The Full Eros》
140×100cm 布面丙烯、油画 2024
在这批新作中,野狗、马、鲜花、贝壳、骸骨被艺术家打碎重组成“新肉身”,铺开一片彼此压制的权力关系战场。
这是一场在身体内部展开的较量,无关动物或人。所有意象只是“美学的一层皮”,在马若骢眼里是“假象”,她真正想讨论的是“美丽兽皮下的谎言和真心话如何交融”。
与过去平扫之上的厚涂、锋利色彩的硬切所流露出的施暴欲和掌控欲相比,新作的气质被驯化得冷漠。构图中若隐若现的“眼睛”(对视),是对观看暴力的批判,也形成艺术家和画的角力。

《别信画家真情意 The artist tells no truth.》
140×100cm 布面丙烯、油画 2024
在近两年的作品中,马若骢有意地“去主体”,以纯粹的直觉和审美,用现实世界的“碎片”来雕琢画面。朦胧的边缘、消失的界线仿佛在无声呐喊:危险正在靠近。
“之所以对画面进行复杂的视觉处理,是因为以前的我更敢简单,现在反而觉得一句话得半真半假地说。”
做图实验阶段,马若骢会在制图软件里对草稿的构图作预处理。转到架上时,一次性抛出颜料打底,再依照空间意识一层一层地向上画。高低起伏间,心力被无限掏空,再生。

《金子是加持我灵魂的萤火虫 Gold is the firefly enriches my soul.》
140×100cm 布面丙烯、油画 2024

马的元素再次成为画中的主角,和告白式的作品名称一样,是艺术家为观众留的一把钥匙。
“我的名字里有两匹马,骢(cōng)的意思是青白色的千里马,这是小学改的名字,寄托了家庭的期望。如果期望算暴力和对抗的话,或许改名也是某种权力斗争的结果。”
在远古岩画中,马通常代表雄性。如今有趣的是,马术成为奥运会中唯一男女同场竞技的竞赛项目,而且不仅运动员不分男女,甚至连马也不分公母。

《夜夜是好夜 Everynight is good night》
140×100cm 布面丙烯、油画 2024
从审美角度看,马若骢觉得马很特别,它的眼睛非常忧伤,光是站着就很忧伤。而新作中的狗和马都与人类史的驯化有关,它们很早就被调教为能被人驾驭的动物。
作为各种竞技场上的生还者,成长于北京的马若骢,自小就洞察到社会化困境下个体的无力。与不合作相比,现在的她坚定地选择创作发声。如果人生没有意义,那便用世俗的成功来“报复社会”,画尖锐的画,画令人恐惧的画。
“作为女性艺术家,我画得越好,我的野心、本事就是对女性主义的一种出力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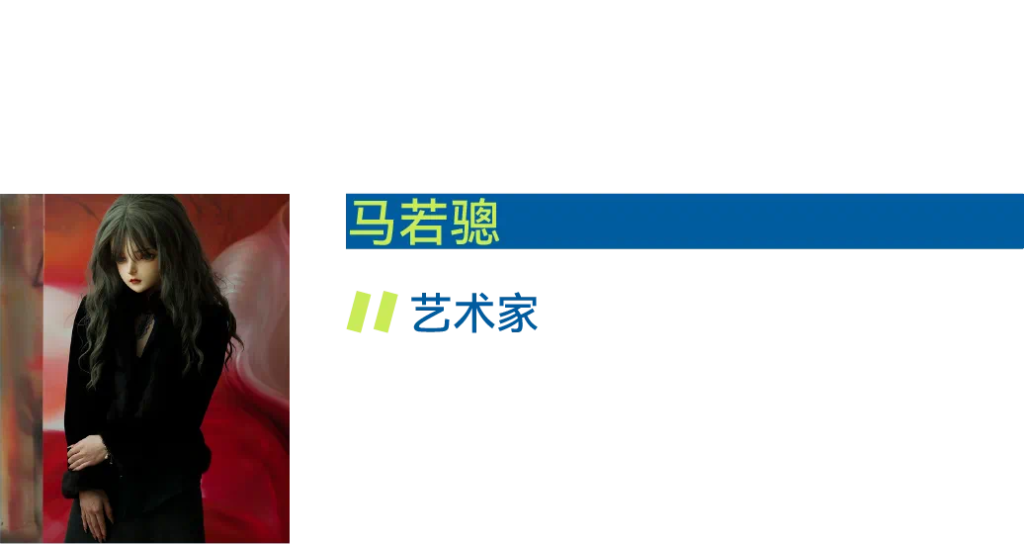

Hi艺术(以下简写为Hi):2024这一年,你的生活状态如何?去过哪些地方,遇到哪些有趣的事?
马若骢(以下简写为马):从年初到年末有好几个展览,基本上都在赶工。7月份我自驾去了趟内蒙,因为有内蒙朋友想举办一个大地艺术节,带我们一起去采风,顺便想为自己之后个展找找素材。我想做和空间相关的雕塑,也和动物有关联,就想去内蒙看看有野性特色的物件。
朋友的草原艺术公社位置不在市区,比较偏远,周围有牧区,草原、沙漠和湖泊。我想去找当地店铺或牧民买一些骨头、皮草、动物“零件”回来做雕塑,但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。直到有一天,我们赶日出在沙漠荒野里晃,害怕车被困在沙子里就下车步行,步行观景的慢节奏让我们意外在沙漠中看到了一具完整的马的尸体,然后我就把它(马的头骨)搬回来了。
老天在回应我的愿望。我想要,我去了,我就看到,我就拥有了。回北京后没有把骨头做成雕塑,而是变成了我工作室(我的精神)里的重要的存在。之后创作的画也潜意识受到影响更有“骨骼感”(《女人的狡兔三窟》这幅画就是刚回北京后创作出来的。)我时常觉得,你信或不信自然的力量就在那里。我的创作里有很多动物和植物的局部,它们拼成了一个新的生命,我从中得到了一种升华。

《女人的狡兔三窟 That woman has no place to go》
140×100cm 布面丙烯、油画 2024
Hi:什么时候开始画这批新作?画了多久?
马:从1-2月开始,画了小一年。每次同期打底5到10幅,画着画着就抛弃了3、4幅,到现在展览一共15幅,废掉的画有小10幅。我觉得画是独立存在的,我画出来的那一刻,是好是坏不由我控制。它好,就是一个好爱人。总也画不好,就得把它盖掉。
Hi:如何理解“丰溢之血”中对禁忌的讨论,和你的内心有什么关联?
马:我在生活中总站在安全自保的领域眺望危险的人事物。对其的迷恋是一种对安全领域的背叛,对权威和规则的挑衅吧,反复在安全和危险之间的那条线上进行僭越。
渴望“丰溢”就是不满足,想要更多。完成了画,还想做雕塑、行为、影像。生活里也是各种不知所措的不满足,比如旅行,我喜欢去南美、非洲、冰岛这些自然环境上危险的地方。我觉得自己本质上是一个很空虚无聊的人,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幸福和安心感,所以只能用其他的东西刺激自己。


“马若骢:丰溢之血”
inner flow Gallery展览现场
我喜欢独处,不擅长(或许是不愿意花太多时间)和人相处。小时候除了空虚无聊之外,就处在一个学业和尊严的竞争环境里,那是生活的主线,你要赢。当时的我无法脱离主线,但成人社会环境里赢的路没有单一的定义。离开了拥有主线任务的学校之后,甚至也很难界定如何算赢,如何算更优秀,如何算更刺激,那时空虚和不安就变得更加具体。
在艺术市场里面,主线任务可能会简单一点,就是刷新展览,刷新成绩,刷新价格、我的作品……我不断画更好的新画,不断输入新鲜血液。除此之外,我是一个没有生活的人。
Hi:人性和动物性在你的画里融合,你如何看待其中的权力关系?
马:权力关系通过构图就能表现。本科到研究生时期我很喜欢米利亚姆·卡恩的作品,landscape里有很多大留白,空旷的背景把人物包裹起来,进行一种压制。作为观众,是代入背景还是代入人?前者是上位者,山包住眼下渺小的人,后者则被大山驱赶着。我的画里围绕眼睛的对视,注视方(画中动物,或者作品本身,或者我本人)和被注视方(观者,他者,收藏者,批评方,路人)就是在进行这场对抗。

《每天都离来处更远 I‘m becoming farther away from my origins every day》
140×100cm 布面丙烯、油画 2024

《权力比爱血肉缠 Power is born of my flesh and blood.》
140×100cm 布面丙烯、油画 2024

Hi:作为点睛之笔,那些情绪时而饱满时而克制的“动物之眼”完成于整幅画面之前,还是之后?
马:其实是同时画。我在画之前就知道画面的终点。所有作品都是先有草稿的,每一块局部的参考都很具体,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发挥。我会进行大量的实验,筛选出最满意的方案。可惜即使有草稿,实际画的时候,会有很多变量,身体(绘画时我的手)和心(作图作草稿时的激情)在进行较量。某一方彻底输了的时候,就是那幅画不满意了要被盖掉的时候。
Hi:从绘画本体来看,这批新作与之前的创作相比有哪些突破?
马:这批画是为这次展览服务的,我希望整体呈现“凶”的感觉,整个空间被画和装置镇住,所以色彩会更浓郁。

《苦夏甜月 Bitter Summer, Sweet Moon》
140×100cm 布面丙烯、油画 2024
Hi:简单描述这些画的创作过程。从构思到完成一幅画的过程中,你的情绪起伏是什么样的?最享受哪一步骤?
马:我习惯连开一排画,并不会画完一幅才画下一幅。而是一批画每天画不同的,然后陆续收尾。最开心的就是画新画,铺底色定位图像的过程很爽。其次是画细节,一幅画到90%的程度开始抠细节,每抠一笔画面都更好更爽一点。
一幅能和我产生好连接的好画,可能一下子就能从20%过渡到90%,连续几个月都在舒服的状态里进行抠细节。但一幅和我缘分不够的画,会在20%-50%的过程中消耗我,超过一个月还在耗我就会盖掉它。
Hi:在平日的创作里,你会从哪些渠道寻找灵感和绘画素材?是否会去各地写生?
马:全网找。我喜欢看无码的动物捕猎视频,非常残忍,但也有美学水准很高的内容,例如蛇绑住一只老鹰的画面,动物流着内脏还在为了活命奔跑的模样。我从来不写生,只拍照片。

《晚安莱斯里 Good night, Leslie》
140×100cm 布面丙烯、油画 2024
Hi:作为画家本人,当你与自己画中的形象对视的时候,你的姿态是什么样的?你如何理解自己和画的关系?
马:肯定会和画面进行比较,它是我的孩子?还是借我的手诞生出来的神明?有时候我在掌控它,有时候画面将我掌控住。有的作品一完成就知道该把它放在展厅的哪个位置。比如具有攻击性的或威严的,得放在展厅尽头,柔情的画放在某个角落。往往那些画得很顺、很得心意的作品,我都感觉不是我画的,而是借我的手生长出来的一种“情谊”。

《Lover I love you》
140×100cm 布面丙烯、油画 2024

Hi:在不断探索自己绘画之道的路径上,你受到过哪些艺术家的影响?请分享你最喜欢的艺术作品及女性形象。
马:卡琳·玛玛·安德森、翠西·艾敏、米利亚姆·卡恩、玛丽亚·拉斯尼格、蒙克,还有雕塑家奇奇·史密斯,影像我喜欢Gillian Wearing,Steve McQueen。分享一个我离开伦敦前看到的最喜欢的展览,是2021年在RA举办的双人展“Tracey Emin/Edvard Munch:The Loneliness of the Soul”,现场让我非常感动。尤其是翠西·艾敏许多作品中告白式的文字影响了我很多,我的作品里后来也用了类似的形式。
Hi:日常生活中,你有哪些兴趣爱好?成长过程中,哪些流行文化对你的影响较深?
马:我喜欢开车兜风(车是我安全领域在社会面上的延伸)、看B级片。高中想自己拍B级片,当时很自满觉得看的片都差点劲儿,想拍点真正让人恐惧的东西。包括我现在作品里的一些恐惧元素也可能源于此。从幼年到现在,我身体里一直有一股愤怒。文学方面喜欢看私小说,那些作者自恋又羞涩地讲自己的故事,又遮遮掩掩的样子满足了我的窥私欲,特别有意思。

《我甚知她 I knew her so little》
140×100cm 布面丙烯、油画 2024
Hi:分享几部你最喜欢的文学、影视作品。
马:罗马尼亚作家赫塔·米勒的自传散文集《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》,谷崎润一郎的短篇小说集《刺青》,还有电影《钢琴教师》,改编自奥地利小说家艾尔弗雷德·耶利内克的半自传体小说。音乐剧《一粒沙》,我每段时间没东西看时或者坐飞机时都会再看一遍,《一粒沙》将女主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的死欲,化成死神对她的求爱,她在死神(死欲)和国王(生欲)之间踱步。我迷恋这种“比喻”的结构之美,其次舞台美学也对我作品在空间里如何布局呈现影响蛮大。
Hi:绘画对你而言,是一种怎样的存在?画家是否是你的理想职业?未来,你希望用绘画做些什么,创作形式是否会变化?
马:绘画对我有疗愈作用。我每时每刻都有很多情绪,绘画能给我及时反馈,画一笔是一笔,其他的艺术形式(比如雕塑,前期准备很长)会让我陷入痛苦无力的循环。同时油画需要干燥的时间,它就像一个温柔的人,不像水彩干得那么快仿佛在催促我继续工作到力竭。油画颜料有呼吸,仿佛在对我说:“你慢慢来,现在我还没准备好,明天可以再爱我一遍。”没错,我每天都会对我的娃娃、骨头自言自语,我喜欢把身边的物品拟人化,对画也在做同样的事。

《爱意充盈 The Full Love》
140×100cm 布面丙烯、油画 2024
除了绘画,最能传达我情感的是现代舞。我的作品很多是有舞台性的,比如这次的展览风格就像一个祭典。比起悉心描绘的日常生活中的小的痛苦,更多是在舞台聚光灯下请求被大家看到剖开内脏的感觉。未来,我的绘画,或者其他媒介的创作可能会结合演出美学来共同表达。
绘画能做什么?就像我看翠西·艾敏的展览,看到她画面的痛苦我也会泪流满面,她的痛苦唤醒了我和她的连接。我的绘画虽然是我个体的私事,但个体的私事其实是集体的私事。我背后的所有标签,我的故事,都不是一个女人的故事,是一群女人的故事。
Hi:作为年轻艺术家,现阶段的你对于艺术是否有终极的目标?
马:其实就是更多更好、更耀眼更有分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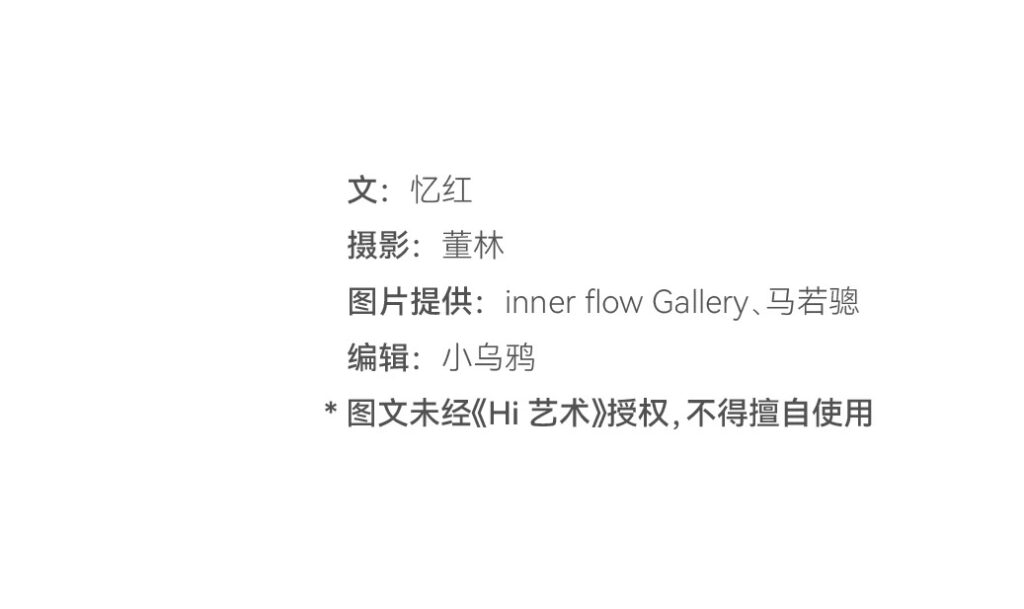

马若骢
1997年⽣于⼴东,成长于北京。2019年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School of Visual Arts取得插画本科学位,2021年于伦敦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取得雕塑硕⼠学位。
个展:丰溢之血, inner flow Gallery, 北京, 2024;种种, 广东美术馆7号厅, 广州, 2024;猎人絮语, 荔院空间, 北京, 2024;驹子, ACENTRICSPACE,上海,2022
群展:跨级社区,油罐艺术中心,上海,2024;第三空间,仚東堂,北京,2024;舍勒绿,仚東堂 ,北京,2024;形与意,元美术馆,北京,2023;隧道双人展, 拟像, 北京, 2023;炽热的前路,inner flow Gallery,北京,2023;崭新的,inner flow Gallery,北京,2023;一片盛大的记忆,久事美术馆,上海,2022;浪潮,方舟画廊,南京,2022;PROXY: MA Sculpture, Cromwell place, 伦敦, 2021; Together It Seams, Standpoint Gallery, 伦敦, 2021; Light, SVA Chelsea Gallery, 纽约, 2019; When black swallow red, LA MaMa Galleria, 纽约, 2019; Out there, Blackbird Gallery, 纽约, 201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