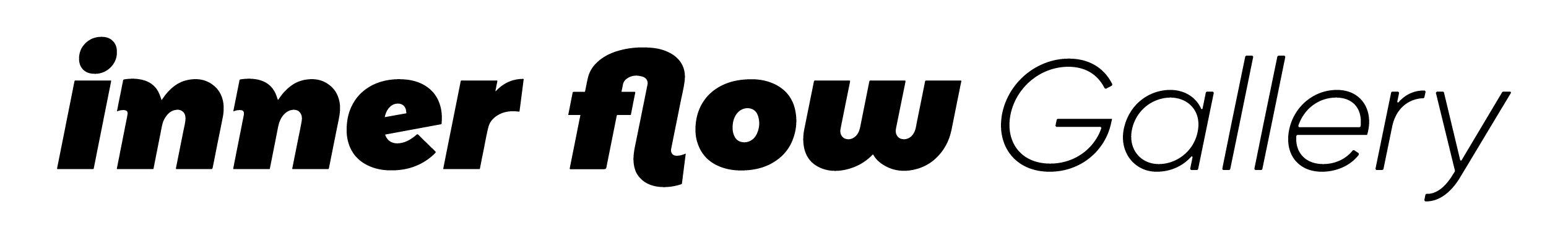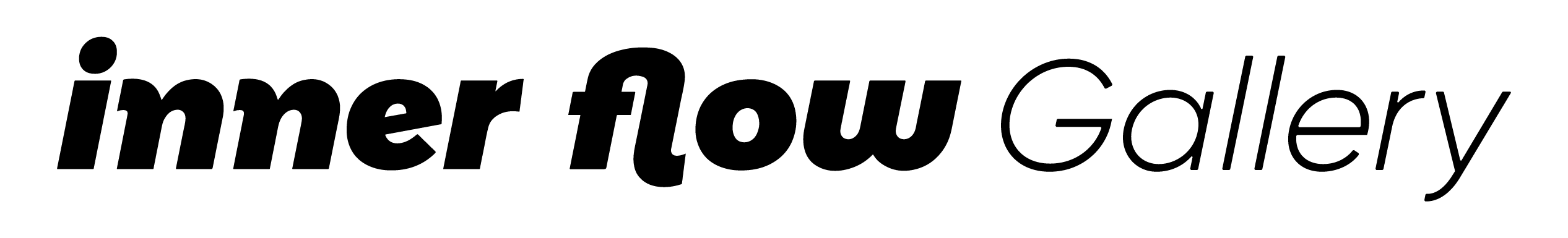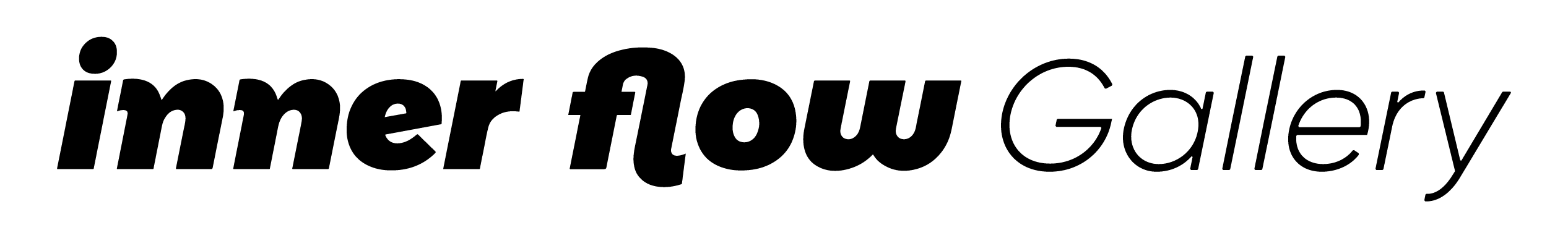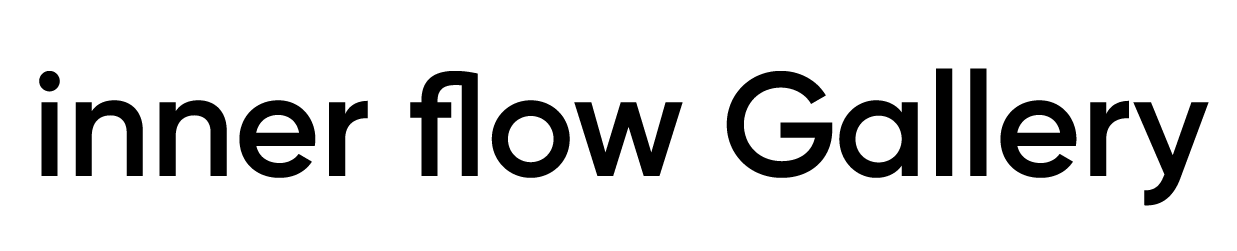全知失能,展览现场
呼应李一凡此次展览“全知失能”中所抛出的问题,inner flow Gallery邀请到数位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进行深度对谈,将陆续于画廊公众号发布。
本篇对谈由著名策展人、研究者杨北辰提问,主要结合李一凡过往的创作经历,对AI的媒介特殊性以及艺术家和AI共生等问题展开探讨。
李一凡:李
杨北辰:杨
杨:你过去的工作主要是影像和纪录片,同时在油画系教学。这次进入AI领域,有什么动机吗?
李:社会事件一直推动我进入艺术,再用艺术反观社会,这是我做纪录片的原因。而教学让我对当代绘画现状有不满,促使我进行内部讨论和反思。现在社会性艺术难做,限制多,我希望换个媒介切入。艺术不仅传达信息,也通过媒介本身表达,就像过去我们不只寄望那些“画得好”、“基因好”的艺术家。
进入AI领域是偶然的。我很早意识到这个媒介会带来新的可能。比如它成本低,用AI创作一幅图像只需几天,而传统绘画可能需要几个月。原本需要工作室,现在只要一台电脑就能创作,所以媒介会带来解放。尽管AI有很多问题,但也带来可能性。大家现在都在谈AI的可怕,既然AI不可避免,我们不如用它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,甚至是抵抗AI的事。
最初我建议一个美术零基础的研究生用AI创作,他不敢相信,我就想带动一下,开始尝试。完全是偶然卷入的,并没有刻意计划。

K_BRID003_500*500H308_P1#LYF09052024
数字绘画,艺术微喷,木框,50×50cm,2024
杨:从卷入到现在展览,经历了多久?
李:最初只是玩玩。前年我在川美做了个小展览,发现AI可以补充图案、图形。这次原本想用AI生成大量图像扔在地上展览,甚至做个像巢穴一样的装置,但后来发现今天这种展览很难做,很难过关。
近年来,真正做社会性艺术或者参与式艺术的,环境越来越难,讯息天花板越来越低,从传统媒介维度思考几乎寸步难行。
疫情后,很多人感叹独立纪录片的消亡,但我不认同。过去我用DV拍摄的初衷就是为了摆脱电视台、电影厂的限制,它更自由。一开始也觉得要一定要拍的摇摇晃晃才是它的本体,后来发现作为个人影像而存在才是核心价值。后来发展成手机、社交网络和网红。现在拍纪录片的人不知比当初多了几百倍,人的主体性是在与社会的交互中建立的,只要按自己的欲望去拍就会建立主体性,消解系统性的权力,媒介的革命才是真正打破传统权威的根本。
同样,我把AI当作媒介工具,而不是去做沉浸式的图景吓唬人。希望每个艺术家都能用它创作,不是靠手艺,而是靠思想。我也推荐给学生,但多数人不愿放弃手上积攒多年的“活儿”。我虽在油画系教学,但不画画,所以可能更适合尝试AI,最终把展览转向了AI创作。

C_MEMORY014_450*600H308_P1#LYF19032024
数字绘画,艺术微喷,铝合金框,45×60cm,5+1AP,2024

C_MEMORY018_450*600H308_P1#LYF19032024
数字绘画,艺术微喷,铝合金框,45×60cm,5+1AP,2024
杨:那未来也会持续在AI领域工作吗?
李:这次展览里有一组海报,内容是虚构的,但文字是真实的。未来我可能会利用AI继续做假展览、假电影节,然后通过网络传播,发展衍生品等等。如今是很多事情难以实现的时代,网络既有距离感,又对具体世界产生不可抵挡的影响。既然很多事情无法通过,那就假装它们已经发生了,有点像开玩笑,但思想不是一样传播吗?

S_POP029_760*530H308_P1#LYF15082024
数字绘画、艺术微喷、铝合金框,76×53cm,2024
杨:你把AI看作解放性、解构性的工具,这和你以前的社会介入创作有关。但历史上,所有新媒介刚出现时,往往会被权力和资本盯上。生成式AI发展才一两年,但已经显现出和权力的深层关联。你在展览中提到利用AI的bug进行创作,这也是艺术家迷恋的点——在强大媒介面前找到让它失效的角度,这种失效和偶然性本身就成了艺术。
李:展览中很多人认为AI作品应该遵守“原教旨”,甚至批评我为什么有拼贴和篡改的部分,他们觉得作品应该“纯AI”,有标准数据库和标准图像。但我却想如何在它的体系中打破规则。我用AI生成福柯、杜尚这些人,并让他们说中文,这本质上就是一种篡改。
安迪·沃霍尔用现成品进行篡改,AI也可以被当作一种现成品。这种篡改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解放。

S_POP024_760*530H308_P1#LYF29072024
数字绘画、艺术微喷、铝合金框,76×53cm,2024
杨:现代艺术史中的艺术家一直在寻找解放的可能性,比如杜尚的《大玻璃》就接住了搬运工的偶然失误,带入作品,证明了艺术家对审美边界的掌控。摄影和计算机生成艺术的早期实验者也迷恋这种偶然性,因为它蕴含不可控性。
绘画本身也是媒介,艺术家和颜料、画布这些“物”一起工作,很难有纯粹主体性。现代媒介让人类与机器的关系更紧密,计算机生成艺术从60年代起就通过输入指令,让机器完成部分创作,把过程交给“黑箱”,而这种不可控性成为艺术的一部分。来到AI时代,这个原理一脉相承。你作为艺术家,和本身做计算机和算法研究的人不同,会有更直接的肉身经验。用AI生成图像和你拍摄影像的过程有何不同?
李:拍东西,物理世界还是给了你明确的体系。在AI的大语言模型中所有算法都存在,艺术家更多是发现者,而非发明者,不像传统的发明,摄影的光圈、快门这些。所以我尽量少用AI图库给的图,或在语言描述上减少步骤,尽量使用我自己的图片内容来做,因为想产生偏离。语言描述会让结果变得极为中庸油腻,不断让结果回到系统认定的平均值。福柯说,你在系统中每讲一次真理,都是对权力的一次重复。在和AI“玩耍”的过程中,这种体验变得极为深刻。

全知失能,展览现场

D.G.T.F003_1200*800H308_P1#LYF02062024
数字绘画、艺术微喷、激光雕刻、木框,120×80cm,2024
杨:AI生成图片的逻辑与图像思维完全不同。它不是简单从图片库中挑选图像,而是通过语言模型重组,例如输入“一个苹果”,它会先解析为圆的、红的、水果,再进行组合。所以AI生成的图像和传统艺术上的“再现”没什么关系,它其实是一种语言模型转化机制,最终生成的图像往往趋于“平均值”,显得油腻。当你给它喂入越来越多的素材,它会学习你的风格,把你也纳入平均值的一部分。
李:没错,你的图库也会成为它的一部分,彼此侵蚀。做久了,AI还会给你返回很多油腻的结果,即使用的是你自己的图像。这时候我会切换到其他软件,比如用PS裁剪,再将留下的特质输入AI,继续生成。不能完全按照它的逻辑走,不然就完了。通常做图需要多次调整。最难的是,我曾尝试生成“中国式现代化审美”的图,开始用了俄式、东欧建筑作为参考,但效果还是不对。输入“中国式”时,AI会给出龙、凤等奇怪的具象物。我才明白,中国式现代化审美是具象的,不是抽象的,它甚至反现代主义,显得非常对称、雄伟。做了几百次后,最后只得到两张满意的图。
当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时,想要脱离具象表达是最难的。

G_MIRAGE002_1600*1100H308_P1#LYF08062024
数字绘画、艺术微喷、裱于纯铝板,160×110cm,2024
杨:影像作品系列系列,你选择的学者中,他们都是大陆哲学脉络中的人文主义者。但AI的大语言模型更符合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逻辑,很多人认为ChatGPT就是一种“维特根斯坦机器”,接近分析哲学的模型。用这种哲学角度理解AI,是否会产生新的张力?
李:我也想过用维特根斯坦和分析哲学来建立边界,甚至用了些海德格尔的思路,但我还是受福柯的影响最大。福柯让一切变得简单,因为他强调话语的虚假性。我们可能就像活在“西部世界”中,权力的结构渗透在每个话语中,谁的声音是真实的很难区分。所以,我在创作时会反复篡改现成品,这也是出于对话语权的警惕和反思。

全知失能,展览现场
杨:很多艺术家都非常珍视自己的主体性,我也很理解你的学生不愿意使用AI创作。毕竟他们学了多年绘画,如果用AI工作,可能会觉得自己辛苦积累的技能都浪费了,主体的原真性和唯一性也受到了威胁。
像刘小东这样的成功艺术家,他做过“绘画机器”的实验,不再担心主体性的损失,因为他已经足够成功了。随着计算机和社交媒体的出现,绘画的基础设施发生了变化。AI逐渐渗透到绘画中,有些艺术家会利用它生成风格化作品。社交媒体上不断流转的图像样式也会进入绘画创作。在艺术和技术的博弈中,尽管艺术家看似处于弱势,但艺术有它自己的逻辑,能把这些技术转化为创作的一部分。
我在思考,AI会不会变成一种风格?虽然现在AI图像很容易识别,但下一步艺术家可能会将AI生成效果融入绘画,成为原真性和唯一性的一部分。你展览侧厅里的作品,每一张都有独特的纹理,这种样式会不会发展成一种新的风格?
李:我也是后来才发现这种可能性。AI更多时候的结构是基于语用,而不是语义关系。AI和人不一样,人会犹豫、怀疑,但AI总是给你明确的答案。你给它任何模糊不清的素材,它都能生成某种图形,形成特殊的肌理,这是我平时没见过的。这些不清晰的部分它都能填补,有种独特的“傻气”。它不会停下来思考,也永远不会说自己不知道。
但在这个过程中,偶然性、缺失性,甚至某种误读都可能产生有趣的效果。比如在侧厅的作品,我最后一个月尝试打印,专门做了7张图,去试验AI生成的“蠢肌理”。这种感觉和我当时用DV试验晃动拍摄,探索模糊画面风格时很相似。我想看看这些肌理究竟是什么样的,带有某种未知的趣味。

M_GARDEN001_1100-900H308_P1#LYF21082024
数字绘画、艺术微喷、木框,110×90cm,3+1AP,2024

杨:没错,现在AI还处于初级阶段,大家都在实验,未来如何发展还不确定,正是实验精神高涨的时候。但如果有一天AI变得像互联网一样普及,我们的态度可能会不一样。
早期有人提出过“鳄鱼能不能跨栏?”的问题,如果AI能回答这个问题,就说明它的语料库足够大。用人类语言的角度理解这句话,多像一句诗啊。所以从这个角度看,AI确实可以产生某种审美和诗意,只不过随着使用,它可能会变得“油腻”。你在创作时,你的艺术史知识和经验肯定也影响了作品,你如何看待这一点?
李:这些经验很重要,因为艺术家总是害怕失去主体性。使用新媒介时,旧媒介的影响也不断干扰我们。当标准方式渗入新媒介,我也担心这种标准化的控制。比如我的助手刘芳展示她工作生成的商业图形,对我来说,这些图都“不合格”。她为哈尔滨冰雕节设计的方案,全是AI生成的。冰雕还没做出来,屏幕上的图像已经生成了,但这些图像只是“再现”,而不是“表现”。正如你提到的“鳄鱼能不能跨栏”,这种生成其实已经进入了某种“表现”的领域。
AI是有可能进行表现的,但人必须很强大,才能抵制它的诱惑。如果没有清晰的方向,很容易被它牵着走,这是一个奇妙的博弈过程。
杨:有趣的是,很多人可能以为你的展览作品是任由AI生成的,毫无控制,其实相反,这是一个高度控制和博弈的过程,是对抗性的。艺术家和媒介之间的关系总是在控制和不控制之间来回切换,随着AI逐渐摸清你要做什么,下一步可能需要寻找新的对抗方式。
李:确实如此,但我对AI进入现实世界的方式更感兴趣,比如虚拟展览,最终实现为可展示的物理形式、肉身体验。很多人只有在作品进入物理世界后才会相信它的价值,实体的呈现仍然非常重要。

C_MEMORY003_1000*750H308_P1#LYF05032024
数字绘画、艺术微喷、铝合金框,100×75cm,5+1AP,2024
杨:AI很有趣的一点,就像列夫·马诺维奇在《新媒体的语言》中提到的数据库电影概念,未来电影制作可能基于数据库操作,而不再是传统的世界再现。我认为AI背后的数据库和万亿级神经网络也是如此。你的展览未来可能也会成为这个数据库的一部分,进入AI的“海洋”。
李:没错,创作过程中AI记录了所有内容。即使删除,数据库里已经有了痕迹,无法真正消除。
杨:这个对抗让AI变得更强,同时也让我们升级了自己的主体性。按照AI的逻辑,它可以无限成长,只要数据足够。我们与AI的互动还在初级阶段,这个过程非常有价值。
李:希望它有用,哈哈。
文字整理:inner flow Gallery 展览研究部

杨北辰
杨北辰博士是一位生活于北京的研究者与策展人,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,同时亦担任MACA美凯龙艺术中心总监。在此之前,他亦曾出任《艺术论坛》(Artforum)中文网资深编辑(2012-2017),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研究员(NCAF,2019-2021),以及普拉达基金会(Fondazione Prada)“思想委员会”(Thought Council)成员(2021-2023)。他曾于全球多个机构策划过展览,如尤利娅·斯托舍克基金会(Julia Stoschek Collection, Düsseldorf)、德国国家文化论坛(Kulturforum, Berlin)、普拉达基金会荣宅 (Prada Rong Zhai, Shanghai)以及上海浦东美术馆(Museum of Art Pudong, Shanghai)等。其策展实践与跨学科的学术方向相辅相成,皆侧重于在当代复杂的技术-生态语境中探讨媒体艺术的可能性。

李一凡
196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,1991年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。 现工作生活于重庆,美院油画系教师。艺术项目:《一个人的社会》、《临时艺术社区》、《六环比五环多一环》和《外省青年》等的主要发起人之一。
纪录片:《淹没》、《乡村档案: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》获得包括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沃尔夫冈·斯道特奖、法国真实电影节国际多媒体作者联合奖、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弗拉哈迪奖、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人道奖在内的数项国际性大奖,以及荷兰IDFA Jan Vrijman Fund电影基金奖和瑞士Vision sud est Fund电影基金奖。《杀马特,我爱你》在国内外文化界引起重大反响。
个展:2008年北京《微观叙事:档案》、2016年重庆《抵抗幻觉——日常生活的仪式》以及2019年广东《意外的光芒》等,较全面的体现了他在中国社会的现状下,用现实本身的超越性去创造新的美学的艺术思想。